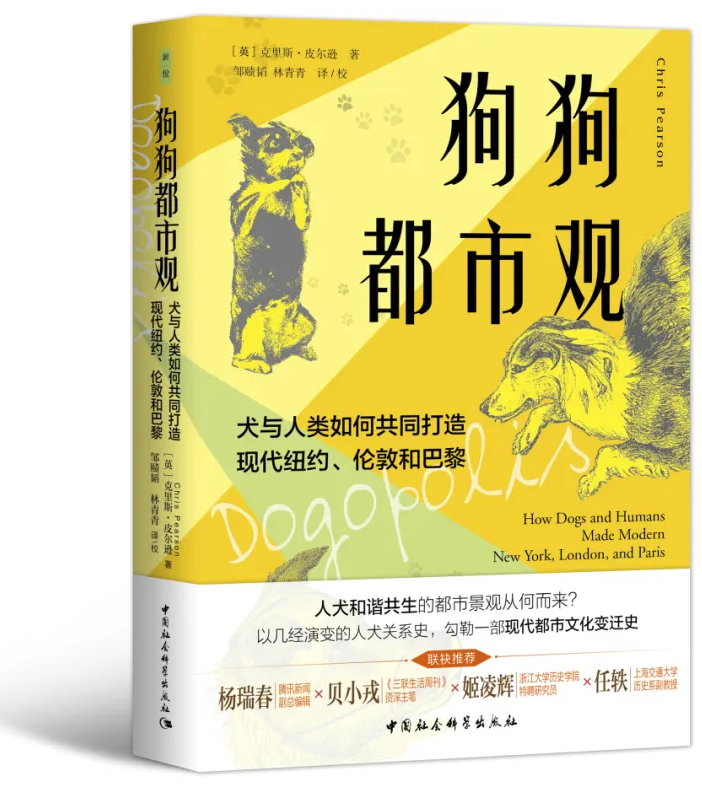
《狗狗都市观:犬与人类如何共同打造现代纽约、伦敦和巴黎》,[英]克里斯·皮尔逊(Chris Pearson)著,邹赜韬、林青青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鼓楼新悦2024年3月出版,436页,96.00元
中学时代曾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书,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中英文对照版。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人与狗的故事,一只名叫巴克的家犬原本已经文明驯化,长期生活优渥,后被偷卖至阿拉斯加,从城市来到荒野,沦落成一只雪橇狗。巴克与新主人之间的感情磨合并不算顺利,巴克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不断历练自己。面对狼群围攻,巴克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敢、忠诚与坚毅。看到这里,本以为是人与狗互相温暖的结局,没想到新主人的死,彻底撕碎了它于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丝留恋,巴克内在的野性同时被唤醒,毅然走向荒野,从此一去不复返。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令我长期以来对猫、狗类动物情怯不已,同时对大自然的力量心存敬畏。
时隔多年,当《狗狗都市观:犬与人类如何共同打造现代纽约、伦敦和巴黎》(以下简称《狗狗都市观》)映入眼帘时,过往阅读经历再次浮现。《狗狗都市观》是英国利物浦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克里斯·皮尔逊(Chris Pearson)的最新力作。他早年曾供职于布里斯托大学、华威大学,研究领域由动物史、环境史与文化史逐渐扩展至情感史、医学史、城市史和全球史领域。简单来说,这是一本关于人类如何在近代大都市养狗的书。作者基于对动物、历史和情感维度的思考,首先对“狗狗都市”(Dogopolis)下了一个定义,“其实就是城市中产阶级居民,对于人与狗在现代城市中应怎样和谐共生的一份跨物种的‘协定’。”(第1页)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跨物种“协定”是如何被人类建构起来的,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对于这段相对容易被人的历史所遮蔽的人犬关系史,作者更倾向于采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人犬关系,及其背后更广泛的情感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某些维度视而不见。简言之,《狗狗都市观》试图展现人类对狗本身以及狗的行为(流浪、咬人、绝育、驯化和排便)的情感反应,而这种情感反应又如何引发了何种行为或举措,从而改变了西方世界人犬的相处模式(388页)。
对于传统历史学者易于陷入线性思维的问题,作者亦有所反思,基本认为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思路和人类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于观察动物的情感活动大有裨益,主张侧重情感历史偶然性的情感史学研究,进一步揭示动物情感史的物质维度与表征维度。很显然,简单的动物史加情感史并不直接等于动物情感史。通读《狗狗都市观》,不难发现,很难用单一的动物史、医疗史、情感史、城市史、跨国史、全球史、新文化史等范畴去框定它,作者也很谦虚,只说是“对动物、历史和情感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仍然未完待续。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是一种近于真理的论断,而这种普遍而自然的人犬关系最早根植于狩猎时代的人犬相依存,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到来,这种关系开始被人类开发的巨大动力所改变。《狗狗都市观》选择伦敦、纽约和巴黎三座城市为案例,认为这些城市是世界历史上人犬关系发生转变的关键场所。(前言第1-2页)实际上这三种城市的选择多少还是“欧洲中心观”或“欧美中心观”的书写惯性表现,应该不存在全球大都市人犬关系对世界其他城市和乡村人犬关系产生“极大影响”的应然关系。仅就东亚而言,东京、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人犬关系便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而与所谓的“欧美世界”并不同步,也不是亦步亦趋,而是表现为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碰撞与调适。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已揭示出物种的跨国、全球流动情形,动物的流动尤为重要。狗狗都市之间的交流本质上是犬类的跨国流动,导致不同犬种之间的杂交、培育与驯化,以及犬类动物携带的寄生虫、传染病也随之而来。值得反思的是,《狗狗都市观》所声称的五大狗狗问题,即流浪、咬人、受虐、思考、排便,实际上自古以来便是如此。问题是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何被人类逐渐认为成为问题,这当然与人类进入近代工业社会、踏入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因此,工业文明时代的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形塑着人犬关系,表现为谨慎的排便犬被文明驯化,反之未被文明驯化的犬只则被人类定义为“流浪狗”。
狂犬病本身不是近代化的产物,古今中外文献均有记载。工业革命以后,乡村人口流向城市,昔日田园犬吠的美好景象被拥挤、污染、粉尘、烟雾等元素覆盖,人口集中在城市,带有狂犬病的犬只一旦咬人便构成一个社会事件,引起城市管理者注目。1830年6月英国率先提出防止狂犬病传播,将流浪狗等同于狂犬病,背后的理论支撑便是当时较为盛行的瘴气理论。加之进化论的影响,人有优胜劣败、狗有贵贱之分,城市化与商业化也催生了犬类服务业、犬类周边产品(狗嘴套、狗络、狗绳、狗粮),狗不再只是一只狗,而是形成了一个产业。
细菌学说的发展重塑了近代人犬关系,造成人犬关系的区隔。1870年代细菌学说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882年巴斯德分离出狂犬病毒,解释框架从“流浪狗=狂犬病”变成“狂犬病毒+狗=狂犬病”。不仅狗咬人有染狂犬病之虞,狗舔人也变成温润而有毒的轻吻。此后相继研制出犬用狂犬疫苗与人用狂犬疫苗,巴黎开始建立巴斯德研究所,亦设有疫苗接种场所,大西洋彼岸的纽约也开始设立巴斯德研究所,将细菌学说接入纽约公共卫生计划系统,反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伦敦却没有跟风,这可能与当时细菌学说的实际影响范围有关,毕竟此时瘴气理论在英国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细菌学说没有对法国、美国、英国产生同步、等效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巴黎、纽约、伦敦三座城市之间的狗狗都市观具有一致性,自然也很难简单得出狂犬病到二十世纪初已被有效控制的结论。
时人认为巴氏狂犬病预防接种法,只是一种增加犬只痛苦的“落后行为”。那么谁来定义先进与落后?如果说巴斯德疗法推进了犬只管理,并未促成根源性的改变,那么又该如何做到标本兼治?如何做到根本解决?长期以来,消灭某种疾病往往是人类一向自认高明的做法,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由亲密变得疏离。实际上,人与人之间需要共情,人与动物之间也需要共情,共情的前提是首先承认人类历史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共存的历史。
工业革命带来动力革命,由畜力、人力转向机械力,人类逐渐抛弃了狗的力量,由实用转变为观赏。从生产力中剥离出来之后,狗的实际地位在下降,一旦流落街头,便有被人类屠戮、盗卖、虐待的危险,滋长了暴力倾向,助长了城市犯罪的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三座城市先后设立了流浪狗收容所扑杀流浪狗,看起来是一种先进的做法,但本质上是一种被隐瞒、遮挡的暴力,溺死、毒杀、棒杀、活体解剖等各种虐杀酷刑上演。权力之外,在市场经济的导引下,杀狗变得有利可图,形成“血色经济”产业链,文明成了野蛮的滤镜。
人与动物之间的共情并非单向的,达尔文的《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便指出狗是具有深刻情感的动物。二十世纪初期,动物对人的情感成为动物保护主义者伸张正义的起点,作为对保护动物舆论的回应,无痛屠宰室、人道扑杀法被发明出来,犬类在戏谑或美化这种“人道主义”之声中被大量消灭。狗狗都市实际意涵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对犬类的规训与惩罚,无论是市政专家基于公共安全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还是公共卫生专家侧重公共卫生出台的《预防狂犬病条例》,莫不如此。多用途犬类经科学驯化从凶猛逐渐变得智慧,此时狗的品种问题被淡化,更强调狗的实用性。但当警犬被用于种族治安时,便不只是治安巡防那么简单,表现为人、狗皆有阶层,而狗有阶层的本质是人有阶层。二十世纪上半叶,警犬只是短暂地融入过狗狗都市。电子防盗警报器技术的推广、发展与应用,逐渐淘汰了警犬的防盗功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伦敦、纽约、巴黎这三座城市才建立起永久警犬队伍,使警犬成为长期存在于狗狗都市中的一道别样风景,既代表公共安全,也代表公共卫生,维持人类世的秩序感。
玛丽·道格拉斯(Dame Ma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中将洁净(purity)的意涵宗教化,不再只是公共卫生维度的洁净与干净,还代表了一种人类社会的秩序感,洁净意味着有序,肮脏则意味着失序,人类社会为了保持这种秩序的有条不紊,便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处理危险力量的滋长。在记者和热心市民倡导下,工程师、医生以及公共卫生专家联合着手清洁城市,卫生间、抽水马桶、上下水道、干净的道路等元素构成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基本场景。一方面人类厌恶肮脏、讨厌细菌、惧怕病毒,另一方面现代都市消费主义盛行,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大城市垃圾清运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而这种试图绝对意义上将人与肮脏、细菌、病毒等危险隔绝开来的做法,也导致人类自身免疫系统在不断迭代更新的细菌、病毒面前越来越弱。
况且在现代都市社会中,人类因内心孤寂往往需要在猫、狗身上寻找安慰,但猫、狗未必真的需要人类。其实这也是未来探讨医疗史、环境史与动物史结合研究的基本立场,必须反思人类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既看到人的主动性,也要看到动物的主动性。从这一点来说,不是“动物+情感+历史=动物情感史”,而是“动物+人类+情感=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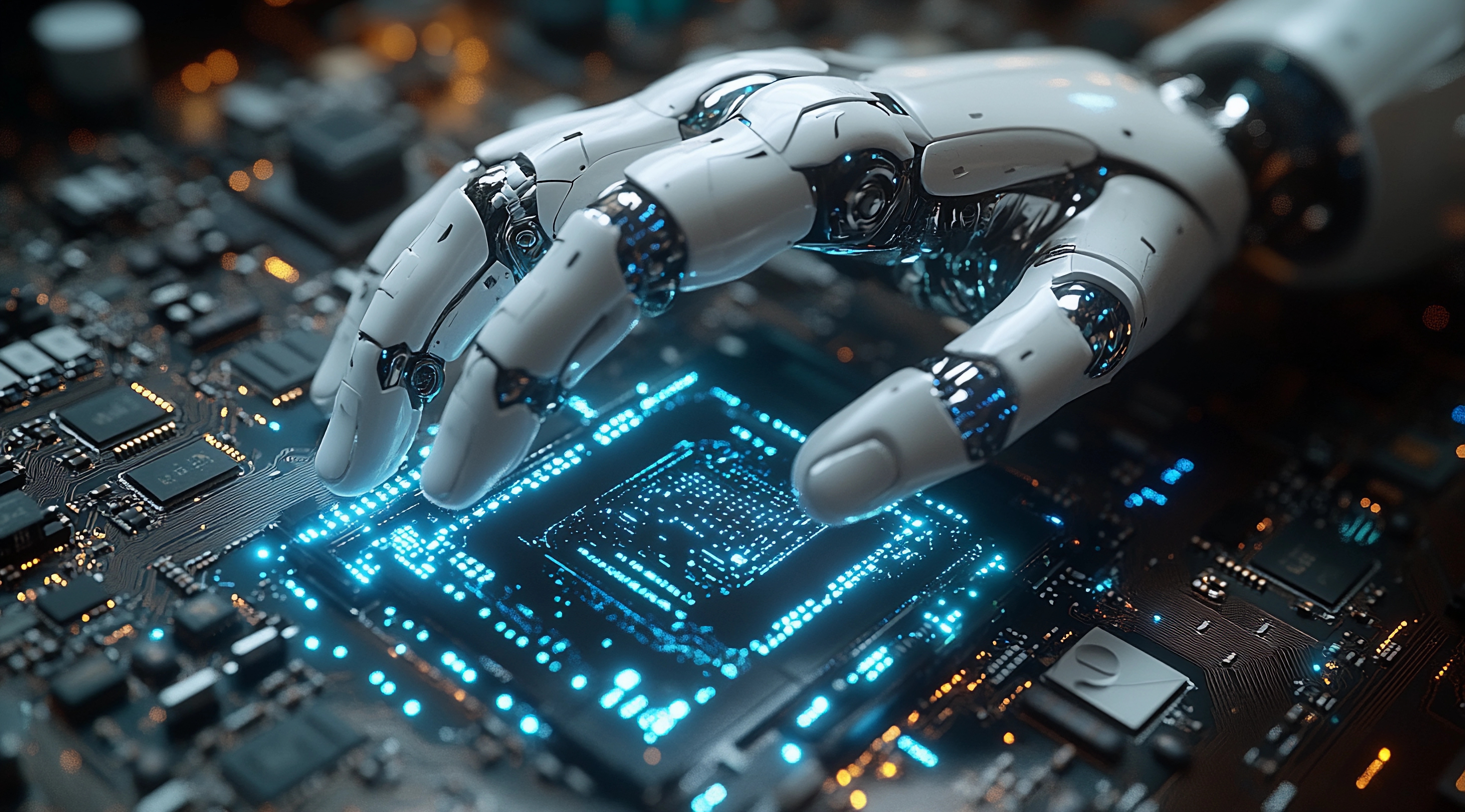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